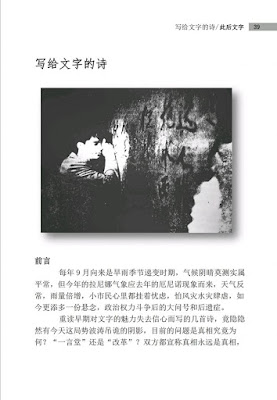搜索此博客
2019年10月30日星期三
木胶及拉叻进行田调工作
1998年, 蔡增聪主任与文协历史组成员同赴木胶及拉叻进行田调工作,抵达当晚, 他们先与木胶当地华社领袖进行交流, 第二天,当地耆老黄南海先生,引领他们到华人义山、故堡遗址及文物馆等地走动。黄先生当时拄着一把雨伞, 缓慢的行走, 边向他们讲述木胶的过去。蔡增聪主任特别印象深刻的是黄先生告诉他,木胶著名的三河中学,校名“三河”是筹设学校当时,他建议采用的;他说既然这所中学是要造福乌也、木胶及万年烟三条河区域的学子,何不就取名“三河”中学。蔡主任后来看了三河中学校友会2017年出版的Three Rivers School:The Pioneering Years 1961-1971 里头特别提到商讨筹建学校时,黄先生当时作为木胶县议会主席, 以及地方社群领袖发言人,担任了会议的协调人(与会者还有澳洲哥伦坡计划的代表Tom Bazeley,他以后成为“三河”的首任校长)。文中也提到He was influential as he was one of the few locals well versed in English。“三河”的校名即是在于这次会议中敲定的。
像黄先生这样对当地历史具有了解的人士,生前没能将他的丰富经历及历史记忆,保留下来,颇为可惜。那天早上, 蔡增聪主任还向他询及对英殖时期统治的看法,以及他所接触过的某位政治领袖的印象, 他给了蔡主任很有趣的回答。
黃南海先生領蔡增聪主任与文协历史组成员看當年木膠武德堡的旗竿座。
拉叻作田调
1998年,蔡增聪主任与文协同仁到拉叻作田调,在当地的华人义山发现了这块墓碑,上面简单的“日人医生之墓”刻文引起了蔡增聪主任的注意。当时虽曾向当地人探询墓主资科,却一无所获;多年后又去了一趟义山,看到墓碑仍在,但疑问仍未得到解答。
这位埋骨荒冢的日本人,姓氏及亡故年份均无记录, 而从简略的中文碑文,或可推测墓碑是由当地华人为其所立。他亡故时身后如有家室或同胞,碑文理应镌有和历及姓名。原以为永远找不到线索,不料最近在查阅史料时,意外在早期拉者政府拉叻官员的报告中,发现一则简讯,提到1914年7月,一位叫Sadaki的日本医生在达叻染病逝世。Sadaki(贞木?贞树?)很大可能性即是上述墓碑的主人,殁年1914年为大正3年。蔡主任问过曾来砂作过研究的山本教授,他表示这种姓氏较为少见。日本向东南亚移民,早于大正即已可开始,在婆罗洲, 以北婆(沙巴)最早,自明治年间已有日人移居;在砂拉越则迟至1930年代初,才看到有组织的日本移民,到三马拉汉地区从事农耕。令人好奇的是在大正年间,竟已有一个日本医生只身到达叻这个偏僻乡镇行医,其目的是什么? 是怀抱一种济世的大爱理想,还是另有其他特殊的因素。蔡主任在Lockard 及Saunders编的Old Sarawak: A Pictorial Story 看到一张题为“1910年古晋的一些领袖”的合照,里头亦有一名仅被称作“日本医生”的人士;从照片拍摄的年份来看,与拉叻的日人医生属于同期;此二人是否是同一个人?从报告对他的死讯的一語带过, 看不出他身份的重要或与砂政府有所关联。战前,日本医生在东南亚行医,虽已见记载,但人数不是很多。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同一时期在砂拉越出现二名日本医生也算是奇特。拉叻义山还有一个较引人注意的现像, 是出现几个以昭和纪年的华人墓碑, 这在蔡主任去过的砂拉越老义山中尚未看过。
这位埋骨荒冢的日本人,姓氏及亡故年份均无记录, 而从简略的中文碑文,或可推测墓碑是由当地华人为其所立。他亡故时身后如有家室或同胞,碑文理应镌有和历及姓名。原以为永远找不到线索,不料最近在查阅史料时,意外在早期拉者政府拉叻官员的报告中,发现一则简讯,提到1914年7月,一位叫Sadaki的日本医生在达叻染病逝世。Sadaki(贞木?贞树?)很大可能性即是上述墓碑的主人,殁年1914年为大正3年。蔡主任问过曾来砂作过研究的山本教授,他表示这种姓氏较为少见。日本向东南亚移民,早于大正即已可开始,在婆罗洲, 以北婆(沙巴)最早,自明治年间已有日人移居;在砂拉越则迟至1930年代初,才看到有组织的日本移民,到三马拉汉地区从事农耕。令人好奇的是在大正年间,竟已有一个日本医生只身到达叻这个偏僻乡镇行医,其目的是什么? 是怀抱一种济世的大爱理想,还是另有其他特殊的因素。蔡主任在Lockard 及Saunders编的Old Sarawak: A Pictorial Story 看到一张题为“1910年古晋的一些领袖”的合照,里头亦有一名仅被称作“日本医生”的人士;从照片拍摄的年份来看,与拉叻的日人医生属于同期;此二人是否是同一个人?从报告对他的死讯的一語带过, 看不出他身份的重要或与砂政府有所关联。战前,日本医生在东南亚行医,虽已见记载,但人数不是很多。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同一时期在砂拉越出现二名日本医生也算是奇特。拉叻义山还有一个较引人注意的现像, 是出现几个以昭和纪年的华人墓碑, 这在蔡主任去过的砂拉越老义山中尚未看过。
河口“拉让”作田调
2005年4月,蔡增聪主任与历史组同仁一起到河口“拉让”去做田调。拉让作为拉让江早期重要的一个口岸,原本存在着一个华人乡镇,如今早已荡然无存。我在中英文献中看到的拉让镇,已无法在这里找到多少痕迹;只有老义山的几座墓碑,还为过去曾经有过的辉煌, 留下少许的物证。几年前曾访问过一位陈女士, 战前,年纪尚轻的她曾与家人生活在拉让,她口中的拉让镇,在记忆开始时, 似乎已处于凋零衰败的境地。当时我还期盼她会突然递给我一张老镇的照片, 好让我能与自己想象中的拉让镇参照。
那一次到访, 在一位土著向导的引领下, 来到早年商镇的遗址,原来店铺所在的地段,其中大部份已崩坍河中。我们在河岸静伫凭吊这座已消逝的乡镇,还留下了一张合影。
乌也作田调
2019年7月10日,蔡增聪主任与文协历史组同仁一块到乌也作田调, 4小时的车程, 经过三道渡口。在峇都停留片刻后, 原本想直奔乌也,但忽然觉得应当进入伊干(Igan)走走, 达罗-马都、乌也我已去过几次, 倒是伊干一直想去看看, 却没有机会。伊干与拉让一样, 战前都曾存在华人的巴剎, 却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些巴剎都消失不见了。
过了渡口, 驱车进入伊干村, 这里的居民看来都很有礼及亲切, 问了几位村民,在他们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了一座有两排小店的巴剎,大部份是经营饮食。本固鲁蔡雄基和一位老哈志攀谈,老哈志向他们透露了有关早年华人在当地活动的一些信息, 哈志先带他们到巴剎对面不远一处华人的墓地,在那里只找到一块还算完好的战前墓碑, 虽然碑文已有点模糊不清;以后他们又跟随他到一位皈依伊斯兰的年长华人的住处, 听说他是目前唯一定居在当地的华人,透过其家人用电话向在乌也的他,转告蔡主任与文协历史组同仁的来意,他匆匆赶回来与他们见面, 他们在小食摊聆听这位原本姓谢的老人家,述说伊干华人的一些历史, 接着还请他带来他们去看早年华人店铺的遗址。 有关伊干华人的史料一直都是文协想搜集的, 但这次之行原本是为年底计划的一场研讨会到乌也进行一些实地考察, 想不到却有了意外收获。此次搜集到的资料虽只是片断, 但多少具有补白的作用,谢老提到早年店家的数目, 与文献记载的也颇为接近。 而谢老个人的信仰及文化调适的过程,其实也可以作为观察华人早期在沿海生活的另一个视角。
伊干在早期的中文记载中多使用了"怡言”或”怡颜”, 推测是来自福建话(闽南)的对音;华人在该地营商,最早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
过了渡口, 驱车进入伊干村, 这里的居民看来都很有礼及亲切, 问了几位村民,在他们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了一座有两排小店的巴剎,大部份是经营饮食。本固鲁蔡雄基和一位老哈志攀谈,老哈志向他们透露了有关早年华人在当地活动的一些信息, 哈志先带他们到巴剎对面不远一处华人的墓地,在那里只找到一块还算完好的战前墓碑, 虽然碑文已有点模糊不清;以后他们又跟随他到一位皈依伊斯兰的年长华人的住处, 听说他是目前唯一定居在当地的华人,透过其家人用电话向在乌也的他,转告蔡主任与文协历史组同仁的来意,他匆匆赶回来与他们见面, 他们在小食摊聆听这位原本姓谢的老人家,述说伊干华人的一些历史, 接着还请他带来他们去看早年华人店铺的遗址。 有关伊干华人的史料一直都是文协想搜集的, 但这次之行原本是为年底计划的一场研讨会到乌也进行一些实地考察, 想不到却有了意外收获。此次搜集到的资料虽只是片断, 但多少具有补白的作用,谢老提到早年店家的数目, 与文献记载的也颇为接近。 而谢老个人的信仰及文化调适的过程,其实也可以作为观察华人早期在沿海生活的另一个视角。
伊干在早期的中文记载中多使用了"怡言”或”怡颜”, 推测是来自福建话(闽南)的对音;华人在该地营商,最早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
诗巫伊干发现前人足迹 村里只剩一位拥华裔血统
一个只有一位拥有华裔血统生活的村落,伊干(Igan)。就像另一个海口城市拉让一样,华人曾经很活跃,但最终因客观因素使然,造成人口外流,特别是他们在原来位置上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已经消失后,只在地方上留下历史的痕迹。
伊干,虽然人口数千,但只能说是一个沿海江口的村落,人口以马兰诺为主,华裔只剩下一个皈依伊斯兰的长者。还有一个年代久远的华人墓碑。
虽然这样,却依然留下了一些的足迹,让后人去研讨早期华人在此活动的资料。
在地理位置上,伊干是属于一个沿海村落,属峇都县辖。但一个国会选区则是以其命名,辖下则有2个州选区,即是达罗和遮摩冷。
而伊干(Igan)小村落属遮摩冷(Jemoreng)州选区。
文协调研早期伊干华人活动
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延续之前在乌也和沐胶等地所做过的调查,并配合将于今年尾举办的《三河华人研讨会》,日前对沿海小镇进行实地考察。
文协田野考察人员,这次来到沿海小村落:伊干,进行调究工作。工作小组是由该会名誉会长本固鲁蔡雄基领导,组员包括文协执行主任蔡增聪、民俗组主任余雪兴、历史组副主任林礼长及组员陈捷雄。
这次的调研工作,虽然没有收集到很多的材料,但是从当地人口述,包括对一座古老墓碑的考察,调研人员对伊干已经消失的华人历史,有部份的了解,并将可做为往后进行各种各样尚可找到的资料。
从这次的实地考察中,发现到可以从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曾经从伊干外迁后裔的口述中,获得更多的资料。
根据文协人员所获得初步资料显示,作为伊干江口一个重要村落,伊干早期原本存在一座规模不大的华人巴刹,过后因各种因素,造成华人人口向外迁移,以致原有的商铺渐渐消失;乃至今天已被许多人所遗忘。
此行历史组经向当地父老查询,搜集到一些有关早期华人在该区活动的口述资料,更意外的收获是在当地父老的指引,找到该处废弃的一块华人墓地,并拍摄了相信乃硕果仅存,年代在战前的一片墓碑。
文协过去曾藉诸报端,征集有关伊干的资料,但始终没有获得回应,这次的实地考察,所获资料虽然有限,但仍属一项突破。
老墓碑见证华人存在
调研人员在当地一名长者哈志哈迪的指引下,找到一座老墓碑,盐木墓碑基本上还保留的很好,但字迹大体上已经很模糊,依稀还可以看到一些不完整的记录。
或许是年代久远的关系,再加上后代没有扫墓等活动,墓碑虽是保留了下来,但字迹已经很模糊,在肉眼上难以获得肯定。
为求真相,本固鲁蔡雄基不惜用手指,亲自去顺着碑上的字迹,顺着字画序了数次,发现到笔画非常接近(蕊)字,所以调研人员暂时将这座墓的主人名字,定为高文蕊。
从模糊的字迹,这座现存唯一的墓碑,是立于民国廿六年,即是公元1937年,2月23日。
从年份来看,这是立于二战日治时期的墓,也就是谢久寿岳父的墓。
谢久寿唯一具华裔血统
如果坚定要说还有华人在这里生活,那么谢久寿该算得上是唯一一个。因为他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过的都是华人的传统生活。
谢久寿,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的穆斯林名字为Ismail Abdullah。他的祖籍是福州人,但只会说闽南话,也是当地唯一会说“唐人话”的居民。
现年77岁的谢久寿,1942年出生伊干,曾经在诗巫中华小学念书,念完三年级之后,因为不习惯诗巫的生活,又回到家乡来。
他的父亲当时是只身来到伊干开店做生意。为何会到这里来,他也不明白,至于父亲的生意最后演变成怎样,有没有兄弟接手,他也不清楚,毕竟年代久远,当时他还年幼。
谢久寿在4岁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1968年年仅24岁时,开始在岸外一间油田公司服务,工作了21年半,退休之后留下伊干,向渔民收集渔获,转到诗巫去卖,直到今天。
曾有6间华裔商铺
伊干有一排6间商店,全部由华人经营杂货生意,从谢久寿的记忆中,经营者除了其父亲 Sia Ting Seng之外,另外还有印像的4家是:Ah Bek、Goh Men、Ha Seng、Kong Ee (名字皆为方言)。
回忆起商店的模样,他表示印像中是一整排高脚店屋,高脚的高度超过一个人,约7尺高。他父亲的店位就在角头间。
“当时,父亲的店位还充作存放渔网用途。当日本人来的时候,将这些渔网全部搬走。”
他回忆说,在1960年代,因为种种因素,华裔外流,这些商店也逐渐的关闭,但原址还留在。原址旁现在由地方当局,建有2栋共4排约20个单位的小贩中心,经营饮食和杂货生意。
谢久寿回忆,在他4岁的时候,看到日本军人在这里活动,他当时还向日军讨东西吃。
在他的回忆中,日本人不友善,不只搬走了存放在店中的渔网,就连要喝椰水,就将整棵椰树砍下来。
华人适应文化融入社区
早期定居在那里的华人,就与大部份华裔占少数的地区一样,娶当地女人及文化的适应,是很普遍的。
就以谢久寿来说,他娶了当地女子成家之后,就融入了当地的社群,整个村里人都视他为一家人。
他称,当时村上有20多户华裔家庭,人口在百多人。除了营商的6户人家,还有的是务农。
对于这一点,从当地一名现年70岁的居民,退休人士,哈迪宾砂拉尼(Hardi B. Shahrani)的谈话中获得印证。
他表示,当初这里的华裔人口百多人,而且还指向两块地段表示,那里曾经都是华裔的墓园。
虽然现在我们只找到一个墓碑,但根据两人的说法,显见当时华裔人口在百人之数,是有可能的。
谢久寿称,当时留下来的华裔,都皈依伊斯兰,除了他的一名哥哥,在近年刚去世,其余的华人后裔都不会讲华语或家乡话。
资料缺乏整理不易
对于伊干的华裔人口流失,也没有留下多少华人活动的遗迹。这里看不到华人生活中最普遍存在的庙宇,否则可从中探索早期华人活动的点点滴滴。
同时,只留下一个墓碑,或许是因为谢久寿还在这里生活,不像其他的墓碑,没有后人的打扫,已经际着时间的流失,而一起荒芜。
文协调研人员,虽然还没有找到充足的资料,但却是一个很好的突破,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相信通过各方的努力,将会让早期华人在这里活动的历史,逐渐的浮现。
订阅:
评论 (Atom)